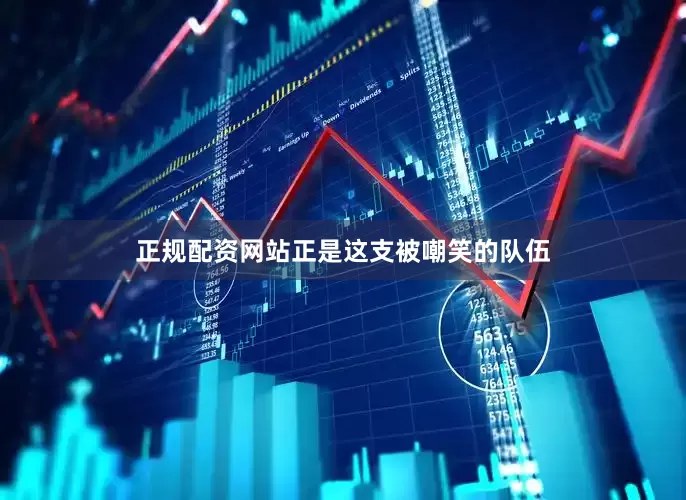老广习惯把今天海珠区称为“河南”,不少人认为是该区位于珠江南岸的原因,其实不尽然。广州市区靠近珠江的街巷叫作“海傍街”,一德路和海珠广场一带旧称“海皮”,江上曾经的两个小岛名“海珠石”、“海印石”,为何唯独珠江南岸地块不用“海”,而称“河”南?这就不得不提东汉时期下渡村走出的大V——杨孚。
杨孚像(图源广东省情网)
展开剩余93%杨孚是史载最早入朝为官、著书立说的广州人。如果说赵佗属于“引进人才”,杨孚就是妥妥的本地俊彦,广州地处边陲,秦汉时期“河南”作为化外之地的城郊,是如何孕育出南粤本土的第一位先贤的?
“河南”的由来
约在六千年前,河南由原来的几个海岛因冲积逐渐连成一片,大致包括宝岗、凤凰岗至七星岗、石榴岗等地(见下图珠江以南虚线面积),即广州地铁八号线市二宫、江南西、晓港、中大、客村等站沿线的狭长地带,再加上凤凰新村和南石头片区,相当于今天海珠区的西北端,主要为丘陵台地,台地边缘有较窄的沉积平原。至秦汉时期,珠江的江面宽度约为两公里,河南因台地迫近江岸变化不明显。
水陆变迁图(虚线为古江岸线)
图源:《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广州》
“河南”的“河”从何而来?
南朝宋《南越志》称:“河南之洲,状若方壶”,又有宋《番禺杂志》载:“卢循城在郡之南十里,与广隔江相对,俗称‘河南’,又作‘水南’”,由此可知南岸之洲命名“河南”由来已久,而且很有可能在“河南”之前叫“水南”。然而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提到,广州“凡水皆曰‘海’”,清《广州竹枝词》又注“广东凡河皆名海”,在古人的心目中,原无“河”的概念。把它理解珠江之南而得名“河南”,却忽略它是“江水四环”的大洲,即使按古时地理位置来命名这个地方,也应名为“海中”或“海南”,绝无称作“河南”的道理。
其实河南一名起于东汉杨孚故居。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广州南岸有大洲,周回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人以为在江水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汉章帝时,南海有杨孚者……其家在珠江南,尝移洛阳松柏种宅前,隆冬蜚雪盈树,人皆异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乾隆《广州府志》引元《旧志》:“(杨孚)字孝元,尝树河南五鬣松于广州城南岸,故名。”印证了“河南”一名与曾在河南洛阳任职的杨孚相关,可能是因他在广州的居所叫河南,亦有可能是其宅前所种河南松柏之故。
位于今海珠区下渡路的杨孚井(图源网络)
杨孚生活的时代
河南台地区的基础是基岩,地势比平原高但地面平坦,可作为城市扩展的地段考虑。与广州城隔江对望的小港成了较早开发的地段。从汉墓分布图看,小港大元岗墓葬群(下图红圈处)延续时间比较长,从西汉前期至东汉后期均有发现,符合此类情况的在珠江北岸也仅有西村石头岗、东山马棚岗等地,这几处在两汉时同属沿江地带。
广州市郊两汉墓分布略图(局部)
图源《广州汉墓(上)》
但当时的河南毕竟是郊区,与城南渡口一江相隔两公里,在杨孚生活的时代,河南的发展如何?
1956年,考古人员在小港路大元岗发现了一座西汉晚期墓,其中一件出土陶壶的盖里刻划了“杨本”二字。“杨本”很可能是墓主姓名,这是迄今广州汉墓中姓名可考的最早的“河南”居民。
陶壶盖内划“杨本”二字
杨本墓还出土了陶酒樽、陶卮、套盒、陶扑满等器。
扑满就是古代的“小猪存钱罐”。汉代刘歆《西京杂记》记载:“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这种存钱罐只有投币口,没有出口,钱币装满后敲碎取钱。杨本的这件扑满,投币口位于上腹部,原应有盖,出土时器内贮存五铢钱40枚。
杨本墓出土的陶扑满
汉代五铢钱是历史上流通最久的钱币之一,其购买力相当稳定。据《居延汉简》记载,西汉晚期,一石粟(约合今天135斤)的价格约为100枚五铢钱,换算下来,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约等于今天的3.4元,杨本的这个存钱罐就有136元了。
1954年南石头纸厂出土了一枚西汉后期的鎏金铜饼。广州汉墓出土金饼极少,目前仅2011年西湾路旧铸管厂一座西汉中期木椁墓出土一枚,放置于女墓主人头端。以上可见当时的河南不乏中产与土豪。
大元岗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墓葬里陆续出土了各类象征财富的模型明器,生活设施设备有陶屋、仓、囷、灶、井,陶家禽家畜有牛、猪、狗、鸡、鸭等,食具有碗、簋、鼎等,是当时广州河南居有所、仓廪实、衣食足的社会缩影。
三合式陶屋 东汉前期
小港路大元岗出土
广州发现的三合式陶屋主要为东汉时期,屋的前堂用于起居接待,侧房用作饲养牲畜和厕所,屋后以墙封成院落。卫生条件比此前的干栏式建筑更优化。
陶囷 西汉后期
小港路大元岗出土
圆形粮仓称囷,方形的粮仓称廪、仓。西汉中后期广州开始出现囷、仓等大型储粮设施的模型明器。
陶母猪(图左)
陶公猪(图右)
大元岗出土的两头西汉后期的陶猪,头短宽,耳小直立,臀部及大腿发育良好。
陶簋 西汉后期
小港路大元岗出土
这种口沿宽、无耳、深腹高足的陶簋是西汉后期始见的新器型,具有地方特色,在两广地区常见。
米仓充实、衣食丰足,就会讲究生活质量,重视精神世界。广州河南也出土了不少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温酒樽、盉、匏壶、四耳罐等酒器。在汉代,人们认为适量饮酒可以通血脉、行药势、御风寒。随葬酒与酒器也是汉代贵族阶层注重养生、渴望延年益寿的观念延及身后世界的反映。折射“升仙永生”终极追求的博山炉,映照“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铜镜等物的出现,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不囿于城墙之内,文化认同与融合已及河南之洲。
陶匏壶 西汉后期
小港路大元岗出土
博山形陶熏炉 东汉前期
小港路大元岗出土
四乳四神纹铜镜 西汉后期
南石头纸厂出土
更多精美文物
杨孚正好成长于岭南地区文明初开的时代。东汉光武帝是新莽时期的太学毕业生,高才好学的他深知学问的重要性,立国之后更加注重文化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兴学办校,提倡儒学,尊重儒生,其后的明帝亦尊奉光武制,崇儒重道。居住在番禺城郊下渡村的杨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见多识广的“河南”人
在科举制尚未诞生的汉代,自汉武帝起,朝廷主要通过“察举”制度选拔人才,被举荐者经考试合格后,由政府量才录用。但这种选举是不定期的。建初元年(76年),对于杨孚这位儒生来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降临了:或许因新帝即位,又或许那两年的天灾人祸,汉章帝诏令各地推举贤良。随后(一说77年),杨孚获得举荐北上京师洛阳,参加“对策”考核,成绩优秀,官拜议郎,相当于皇帝身边的高参和顾问。
杨孚提出其中一个重要主张为“吏治必务廉平”,当时不少地方官员以玳瑁等中原地区少见的特产“竞事珍献”,以此笼络、贿赂京官。杨孚在洛阳任职期间,为使人们了解真实的岭南风土物产,以及供交趾刺史部及各级属员资政之需,撰写成《南裔异物志》,又故意以“异物”命名,实则是表达“讽切”之情。未料这本书却成了迄今可见的粤人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地域性物产志。另外《异物志》运用藻言韵语,便于诵读。屈大均评价它为岭南诗歌之始, “广东之诗,实始于杨孚”。
《广州大典·岭南遗书》所辑《异物志》
(图源广东省情网)
书中记载的物产不止于岭南,还涉及周边地区和海外国家,如日南、九真、交趾(位于今越南)、扶南国(位于今柬埔寨)、金邻(位于今泰国西南部)、斯调国(位于今斯里兰卡或印尼爪哇岛)等地,所列之地正是《汉书》所载海上航线所到之处。番禺面向海洋,水路便利,日常可见海外货物和人力流入,从下图统计表可见,早期的胡人俑多在河南发现,反映广州河南的大户人家较早使用“外佣”。
胡人俑座灯统计
图源《广州汉墓出土人物俑的发现与研究》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到达沿海诸郡不易,杨孚所写的异域风物主要应当还是从他赴京前在广州河南生活时采访所得。而且他极有可能亲眼见到甚至接触过这类外来人口,他在《异物志》中称他们为“瓮人”,并记载:“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强勤力。”可以猜测一下,杨孚关于海外的见闻,除了请教出海“见过世面”或从事交易的居民,会不会也偶尔从这些外籍家政人员或庄园保安身上获得第一手资料呢?
陶托灯俑 西汉后期
小港新村刘王殿出土
陶托灯俑 东汉前期
小港路大元岗出土
“河南”的一方水土成就了杨孚,“南雪先生”亦让“河南”美名流芳。欢迎到“人间镜像——广州汉晋墓葬的生命叙事”展厅,在文物里继续挖掘更多“河南”的印迹,或者找寻你现在广州生活、工作的所在地,两千年前,是沧海,还是桑田。
参考文献
黄小娅《广州“河南”地名说》
陈泽泓《从杨孚〈南裔异物志〉一窥汉代海外交往》
王丽英《杨孚〈南裔异物志〉的价值》
覃杰《广州汉墓出土人物俑的发现与研究》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下册)》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发布于:北京市免费配资开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